主流媒體 山西門戶
山西新聞網不良信息舉報:0351-4281485
“長年變法”,他血管裡奔涌著年輕人的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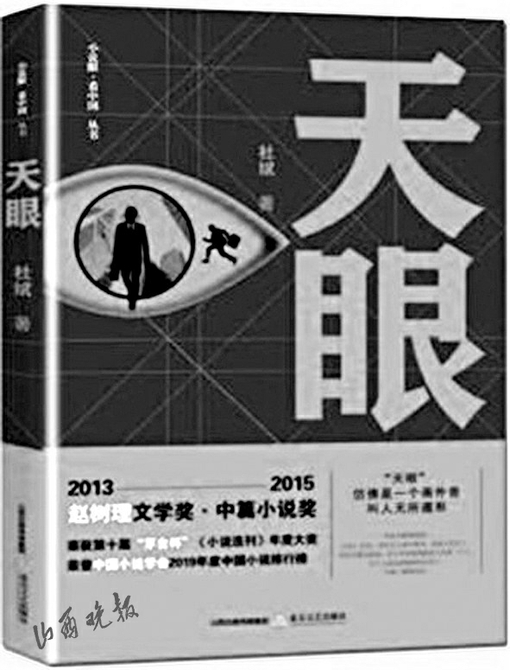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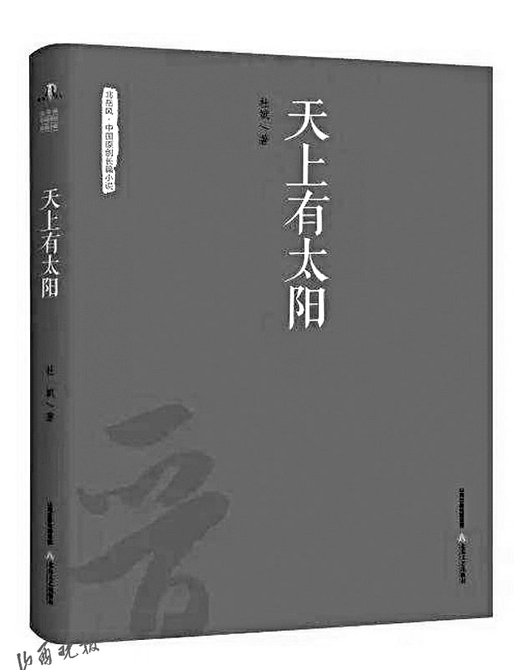
有論者言,山西文學有一種“衰年變法”的現象,就是說很多人在退休之后煥發出了創作的“第二春”,表現出更旺盛的創造力。省作協主席杜學文在解釋這一現象時將“衰年變法”稱為“長年變法”或“高年變法”,他認為這些作家雖然年歲有長,但生命力並未進入“衰”狀,反而日見其盛。他還舉例說:雖然從年齡的角度來看,杜斌當然是大於李國濤等人。但從對文學的執著而言,他們實在是同一種人。
李國濤曾任《山西文學》雜志主編,擅理論與評論,但因為眼疾,不能長時間閱讀,就轉向回憶,以“高岸”的筆名創作小說,長、中、短篇聯袂接續,以至於不明就裡的人以為“高岸”是一位頗具實力的文學新人。那麼,杜斌是誰?
對很多人來說,杜斌是一個“新人”,是最近幾年才突然活躍在山西文壇的,作品很多,獎也不少:2016年,中篇小說《天眼》獲“趙樹理文學獎”﹔2018年,長篇小說《天上有太陽》被《長篇小說選刊》選載,並榮獲“第三屆長篇小說年度金榜(2018)特別推薦獎”﹔2019年,中篇小說《風烈》被《小說選刊》轉載,並榮獲第十屆茅台杯《小說選刊》年度大獎,入選2019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2020年,中篇小說《碑上刻什麼就等你來定》再被《小說選刊》2020年第4期轉載。
長、中、短篇小說接二連三地發表,並被轉載,有的還獲得了比較重要的獎項,這便是杜學文所說的“長年變法”吧。
其實,杜斌是一個“舊人”。1956年生,永濟人,中國作協會員,1973年開始創作,憑詩歌《荒山穿上翠綠衣》踏入文壇。1978年開始發表小說《一把胡子的變遷》《你是什麼兵》《山村不夜天》《飢餓》《火警》等。如果從出現的時間點來看,杜斌應該與被稱為狹義的“晉軍”是差不多時代的人。但是,當杜斌正在逐漸被人關注的時候,因個人原因,1984年起遠離文壇。
遠離並不是離開。文學的情結一直在杜斌的內心躍動,2011年,杜斌回歸。幾年間,接連完成中短篇小說《螳螂謠》《天生我材必有用》《無形刀》《狗日的羊肉泡魚翅》《投標前戲》《天眼》《劉局過生日》《清明時節》《碑上刻什麼就等你來定》,長篇小說《天邊一片火燒雲》《活法》《葉變花》等,並出版小說《天上有太陽》和小說集《天眼》。
務農、當兵、做官、辦廠、經商,人生百味,該嘗的不該嘗的杜斌全都嘗過。正因為有著如此豐富的個人經歷,他的作品極度貼近現實的表達令人驚嘆。當他重新拿起筆時,人們便發現了一個具有獨特風格的作家。
在60多歲這個年齡,掀開創作新篇章,重新以一個作家的身份出現——山西作家杜斌,值得尊敬,值得書寫,他的創作經歷更值得解讀。於是,山西晚報專訪了三晉文壇“長年變法”的代表杜斌。
第一位被全國頂尖選刊選中的山西作家
山西晚報:您近幾年創作的作品非常集中且質量高,咱們的採訪就從您的作品開始吧。先來說說您回歸文壇不久就獲得“趙獎”的中篇小說《天眼》,這是部商戰題材的作品,創作於什麼時候?
杜斌:《天眼》創作於2014年,寫了兩三天,修改了一個多月,2015年發表在《黃河》第4期上。小說以當代商戰為題材,以天眼作比喻,想表達人在做、天在看的主題思想。
山西晚報:商戰題材山西作家創作得比較少。
杜斌:是啊,我寫這個題材是因為小說有我個人的經歷。我曾經下海經商,做太陽能產品,作品中的主人公張高美、劉成等人就在我身邊,再說得准確一點,他們都是我領著進入太陽能領域,並手把手教他們如何做產品,如何聯系客戶,如何投標,如何做工程的。他們在商場上摔打磨煉成熟了,有了資本,就自立門戶當老板,反過來和你爭搶分食市場蛋糕,在商場上這樣的人很多。
山西晚報:正因為您親身經歷了,所以寫出來更真實、更吸引人。當年知道這部作品獲得2013-2015年度的“趙獎”時,是怎樣的心情?
杜斌:我沒想到《天眼》能獲得“趙樹理文學獎”。在我的心目中,“趙樹理文學獎”像山一樣存在,雄偉屹立,高不可攀,是山西作家的最高榮譽。我能得到如此榮譽,有運氣的成分,首先我遇到了黃風這樣的《黃河》好主編,他一雙慧眼把我從沙裡撈出來﹔其次,我還碰到了有眼光有水平的評委。獲獎后,“登斯樓也,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但心情總的來說還算平靜,不是“趙獎”不重,主要是我這個人經歷得有點太多,早已沒有了“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豪情。但我還是十分感謝“趙獎”的評委對我的加持和鼓勵。我想我不會辜負他們。
山西晚報:2016-2018年度的“趙獎”您也有入圍,是嗎?
杜斌:入圍的是我的長篇小說《天上有太陽》,它是我多年傾心打造的一部作品,代表了我當時的文學創作水平。這部作品2018年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后,《黃河》雜志社還為我舉辦過研討會。也正是《黃河》對《天上有太陽》的滋養澆灌,才讓這朵小花得以綻放,《長篇小說選刊》選中了這部作品刊發。
山西晚報:被《長篇小說選刊》選中是怎樣一個分量?
杜斌:我是《長篇小說選刊》創刊以來第一位有幸被這家全國頂尖選刊選中的山西作家,還有幸和劉亮程老師的《捎話》刊登在同一期。刊發《天上有太陽》的那期《長篇小說選刊》卷首語這樣評價:如果說劉亮程“《捎話》的姿態是飛翔的話,那麼《天上有太陽》則是在大地上行走”。“小說以出色的敘事能力,書寫了豐富斑駁、寬闊復雜的中國經驗,具有強烈的生活質感和鮮明的現實主義品格”。之后,《天上有太陽》的榮譽接踵而來,年底又榮獲第三屆長篇小說年度金榜特別推薦,那一屆的上榜的作品中有梁曉聲老師的《人世間》和陳彥老師的《主角》,后來這兩部作品都獲得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能和他們一起上榜是我的榮耀。
山西晚報:但是《天上有太陽》最終沒有獲“趙獎”,遺憾嗎?
杜斌:是很可惜啊,《天上有太陽》是在終評時落選的,但這一方面說明《天上有太陽》還需要細心打造雕刻,也從另一方面証明我們山西文學的高原上珠峰林立,這是我們山西的驕傲。在此,我衷心祝賀獲得“趙樹理文學獎”長篇小說獎的作家們,他們就是我眼裡的高山,我要向他們學習。
獲《小說選刊》年度大獎 與文壇巨擘同台領獎
山西晚報:近幾年您頻繁創作,也頻繁獲獎,令您印象最深的獎項是什麼?
杜斌:是我的作品《風烈》獲得的第十屆“茅台杯”《小說選刊》年度大獎中篇小說獎。2019年12月6日,這個獎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頒獎典禮,這是由中國作家協會《小說選刊》雜志社和貴州茅台集團共同舉辦的。正像《小說選刊》主編徐坤老師在致辭中講的那樣,中國文壇如今有兩項名滿天下的文學大獎:即茅獎和茅獎,前一個是茅盾文學獎,后一個是茅台杯文學獎。在這屆茅台杯獲獎者中,有五位作家獲過茅盾文學獎——王蒙、徐懷中、莫言、徐貴祥、遲子建——能和這些文壇巨擘同台領獎,我三生有幸。
山西晚報:現在都能感受到您當時的熱血沸騰。
杜斌:是啊!在頒獎典禮上,當我看到85歲的作家王蒙先生為90歲的作家徐懷中先生頒獎時,熱淚盈眶。那個畫面永遠浸刻在了我的心坎。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我的明天。我才60多歲,我血管裡奔涌燃燒的是年輕人的血啊!燃燒吧,文學!燃燒吧,我!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火。翱翔!翱翔!歡唱!歡唱!隻有歡唱(激動)!
山西晚報:“茅台杯”給《風烈》的授獎辭是什麼?
杜斌:說“《風烈》以一所民營職業培訓學校為切口,讓人窺見更為廣闊的世道人心,重現了譴責小說的風貌。尤為可貴的是,作品描繪的不是善與善之間不可調和的較量,也非善與惡之間不能相容的斗爭,而是揭示人自身所處的一種不穩定的平衡狀態,呈現欲望和性格如何戲劇化曲線波動。因而,《風烈》既不是令人震撼的悲劇,也不是試圖簡單地弘揚正義,它冷靜、客觀,辯証地呈現了人性的風景。”
山西晚報:的確是一語中的,看完《風烈》就是這樣的感受,能讓讀者通過民營職業培訓學校的辦學經歷感受世道人心。《風烈》還有其它榮譽嗎?
杜斌:去年12月底,中國小說學會2019年小說排行榜揭曉,最終評出30部上榜作品,《風烈》忝列其中。一年內一部作品兩次獲得榮譽,我的心情,呵呵呵呵,文字太蒼白,找不到准確的詞語表達(笑)。
為了生活,擱筆經商 為了精神,又開始了文學夢
山西晚報:當作家是您年少時的夢想嗎?您是怎樣走上文學創作之路的?
杜斌:年少時的我,是夢想當像華羅庚一樣的數學家。初一時,我的數學是全班最好的。無奈,那個年代,我像所有的學生一樣,面對前途,有種“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的迷茫與絕望,“我欲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就在此時,我們村的王西蘭(我省著名作家——編者注)橫空出世,亮瞎了我的雙眼,啊哈,青山遮不住,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義無反顧地步王西蘭的后塵,放棄數學,踏上文學的征途。
山西晚報:那是數學家變成了作家,從什麼時候開始發表作品的?
杜斌:王西蘭像一盞燈,讓我在茫茫暗夜中看到了一條光亮的康庄大道。歪打正著,現在回想起來,我真的不知怎麼說好。在這片富饒、博大、深沉的土地上,我原想喝一滴墨水,它卻給了我一個五千年的文化海洋﹔我原想得到一塊蒸饃,它卻給了我一生享用不盡的寶貴礦藏﹔我原想得到生命的一抹綠色,它卻給了我紅花遍地綠樹成蔭金風送爽白雪皚皚的一年四季。當年,我一頭扎進文學的海洋裡,一年多的努力,我的願望結出了一個花骨朵,1973年我發表了第一首詩歌《荒山穿上翠綠衣》,后收入197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西詩選》。1977年我入伍服役來到長治,在繁重的大比武空隙,我頭懸梁錐刺股般地在文學的叢山中揮汗如雨般跋涉,我的辛苦得到了報酬,1978年《長治文藝》創刊號發了三篇小說,就有我兩篇:《一把胡子的變遷》和《山村不夜天》。
山西晚報:您早年創作的作品集中於什麼題材和內容?
杜斌:我早年的小說大都是從我記憶中的農村挖掘出來的。1979年起,身上沾染了些許城市氣息的我,小說題材也漸漸多樣起來,1980年《汾水》發表的一個短篇小說是我第一個城市題材作品,可我記不住題目了(笑)。隨后還寫了幾篇消防部隊題材的小說。
山西晚報:在還有創作熱情的時候,為什麼會輟筆遠離您熱愛的文學?
杜斌:那個年代,生活中的我沒有選擇的權力,生活的逼迫和無奈,使我不得不遠離我熱愛的也給我帶來美好前程的文學。剛出體制時,我曾口出狂言,要像魯迅那樣靠稿費生活,但現實太骨感了,我沒有魯迅先生的才華和幸運。一出體制,我就啥也不是,連一株野草都不如,野草還有個它生長的一撮土,我呢?我就是天上的一朵雲,是風中的一粒塵埃,是垃圾堆裡的一片碎紙屑。理想是西北風,光喝西北風會死人的,我需要解決溫飽問題,“爬格子”爬不出米面,作家不能當飯吃。我不相信除了文學,我就活不下去。天底下沒有餓死的麻雀。於是,沒有選擇的我,靠著自信自負,毫不猶豫地跳進了商海,是被淹死還是能駕一葉扁舟自由航行,當時的我沒想過。我在商海沉沉浮浮到今天,好在還活著,活得還算瀟洒。
山西晚報:在那些“消失”了的日子裡,您是去經商了?
杜斌:我骨子裡是個不安分的人,我離開太原到長治開公司,到晉城建鐵廠,到海南收購公司,又回到山西煉焦炭,搞外貿,出口德國,闖蕩美國,資本運作,收購國企,像頭野牛,橫沖直撞,紅紅火火了十多年。
山西晚報:生意做得好好的,為什麼又拿起來筆?
杜斌:文人的情懷,是天山雪,是玫瑰花,是迷魂湯,它讓我童心明澈,同時又泛濫成災。其實在我45歲那年,我曾為了朋友舍棄萬貫產業,自我銷聲匿跡。好在我像小紅孩一樣愛胡折騰,在珠海,不到兩年,又成就一番事業。但我是一個追求完美的人,物質生活不是問題時,精神生活的需求就不時地敲擊著我的大腦,在珠海朋友的鼓勵下,我又做起了文學之夢,拾起了放下近三十年的筆。
作為一個寫作者 我的經歷是老天爺賜的一筆財富
山西晚報:2011年,您已經五十多歲,再開始“爬格子”覺得辛苦嗎?
杜斌:我沒有路遙、陳忠實那樣用生命來寫作的精神,我是玩高興。“爬格子”對我來說是一種精神和肉體上的雙重享受,那是我又一個能掌控的自由世界。
山西晚報:您當過兵,開過礦,經過商,這些經歷為您再創作提供了豐富的土壤,是嗎? 近幾年集中創作並獲獎的作品,如《天眼》《天上有太陽》《風烈》《碑上刻什麼就等你來定》這些作品都來自於您的個人經歷嗎?
杜斌:我很感謝生活。我走過的路,天上地下,大河小溪,其長度和寬度,常人難以想像,什麼樣的罪我都受過,什麼樣的福我都享過。作為一個寫作者,這又是老天爺賜給我的一筆財富。我熱愛它,珍視它,擁抱它,享受它,品味它,解剖它,探究它。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它裡面的一朵花。
山西晚報:豐富的人生經歷,肯定也是讓您飽經滄桑的,但您寫出的小說卻沒有繁雜和夸張,一派真實,怎樣看待自己這樣的寫作風格?
杜斌:你的眼光很毒啊。我的作品大都有我的親身經歷,現實感強,故事性強,活色生香的別人體驗不到。我想我會把這種風格保持下去。
山西晚報:為什麼偏愛這種現實主義風格?那您作品中的人物應該都有原型,對嗎?
杜斌:由於歷史的原因,我深受俄羅斯文學和法國文學的影響。由於地域的原因,我深受趙樹理問題小說的影響。由於文化的原因,我又深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擔當意識的影響,反映到寫作中,就是自覺地對現實主義產生偏愛,成為名副其實的現實主義者。我認為,現實主義的寫作者,首先就是布道者,其次是批判者。不同的時代,產生不同的作品。作為一個現實主義寫作者,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的歷史時刻,絕對不會辜負現實賦予自己的使命,要把自己的才情、格局、智慧,毫無保留地、義無反顧地投入到歷史巨變的長河中去,讓自己的想象力、理解力、描摹力、概括力,發揮到極致,創作出更多活色生香的、超強生命的、謳歌新時代的好作品。我的人生經歷,決定了我看到的社會現實生活中的原始的丑陋的陰暗的東西肯定很多,我對它們深惡痛絕,恨不得用文字的手術刀,將其剔除干淨。所以我的作品中的人物都來自於生活,都有原型。
山西晚報:的確,您的作品吸引人,也是因為真實。而且除了帶有生活意味的、煙火氣息的、生命質感的內容,每部作品都有價值判斷的現實世態。如《天眼》中“人在做、天在看”的主題思想,《碑上刻什麼就等你來定》中的忠義文化特色等,為什麼每部作品都要有這樣的思考與價值觀的呈現?
杜斌:小說不是素描,它要對生活進行升華改造。生活不能僅僅沉浸在批判中,生活需要亮色,需要向上,既然是讓人學習享受的作品,就要給人以生存的希望和力量。
三晉文化的精髓在我的創作中是神一般的存在
山西晚報:說到最近剛刊發在《小說選刊》上的《碑上刻什麼就等你來定》,其實走的是愛情路線,您的小說主要取材於您親身經歷的商戰風雲、人生浮沉,似乎多英雄氣概,少兒女情長,為什麼換了主題?而且這個愛情故事有“義”這個情結在裡面,為什麼?
杜斌:我的家離關老爺家十多裡地,從小就被隨處可見的關帝廟、民間傳說的關公形象熏陶浸染。關羽的言行,始終與“義”連在一起,為了“義”,他可以快馬飛刀,令人頭落地,也可以勒轉馬頭,讓敵首逃跑﹔可以勇斬強敵,轉瞬取勝,也可以心頭不忍,刀下留人﹔可以不睬軍師,自行其事,也可以俯首聽命,忠心效力。在他的心目中,“義”高於一切,勝於一切。我也清楚地知道,關羽的忠義思想裡有太重的個人義氣成分,這種負面的東西,也十分自然的對后人包括我也帶來過負面影響。我的兩次大落都是太重個人義氣的結果。但是,不可否認,在長期崇尚關羽忠義思想的歷史演變中,關公的文化底蘊,集中了很多優秀的精華,也不斷融入新的文化內涵,值得我們在繼承中發展和揚棄。特別是看到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關公的忠義思想中的一些進步的、價值的成分,正在一步步被金錢吞噬,我很焦急,不想讓關公的忠義思想中的這種精神絕跡,商場上不好表現,寫出來就是大傻。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經常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無奈之下,我隻好借用愛情的鸚鵡嘴來歌唱它,於是就有了《碑上刻什麼就等你來定》。
山西晚報:怎樣用愛情表達“義”?
杜斌:用《小說選刊》副主編李曉東老師在為《碑上刻什麼就等你來定》寫的評論中的話吧。“愛情的結構物,除了情,還有義。情義無價,情者,心相知、意相融也﹔義者,為對方犧牲奉獻也”,“陳少志、劉青山、王九九、張倩是生活在現代的人,但他們成長的環境,也即蛇城,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俠義文化最深厚地之一”。
山西晚報:對啊,您小說裡常會用到“蛇城”這個城市名稱,熟悉的人一看便知是指太原。而在作品的講述中,蛇城所蘊含的,不僅是太原,而是整個山西,三晉大地、三晉文化的精髓。故鄉在您的創作中是怎樣的存在?
杜斌:神一般的存在。
山西晚報:您希望《碑上刻什麼就等你來定》帶給讀者怎樣的感受?
杜斌:就像我在《小說選刊》創作談中寫的那樣,“帶著真愛,帶著執著,帶著春天,帶著苦難,帶著坎坷,一點點,一點點,把它煥發出來。《碑上刻什麼就等你來定》就是這一點點中的一點點,願這一點點中的一點點能給讀者一點點享受。”
山西晚報:您作品裡的山西味兒很濃,《風烈》裡的傅山和頭腦、過油肉和刀削面、革命老區,《碑上刻什麼就等你來定》中的晉劇和背棍,還有貫穿全文的槐樹,這些都能讓讀者看得見山西,感受到鄉愁,這是您自然情感的流露,對嗎?
杜斌:沒錯。我有個想法,我也是這樣做的,隻要是發蛇城為背景的每一部作品,我都會想方設法把我們山西的文化、民俗、名勝等優秀的東西巧妙地糅進去,也算是做個軟廣告。
山西晚報:您多部小說中提到的“洽洽河”,其實就是汾河,為什麼給它起了這樣一個可愛的名字?
杜斌:我沒能力給汾河叫一個好名字。正好有天,我在美特好超市買了一袋洽洽瓜子,瓜子就是供人無聊時品嘗享用的,我的作品何嘗不是如此,所以汾河在我的作品裡就成了像瓜子一樣供人享用的洽洽河。
山西晚報:您的創作速度很快,當人們還在談論您的一部新作時,您已經又完成了一部更新的作品。在這個年齡,您是如何做到如此高產的?
杜斌:我幸運,我的生活是我創作的富礦,取不盡,挖不絕。文學是需要天賦的,我可能有這方面的天賦吧。
山西晚報:近期有什麼創作計劃?
杜斌:疫情期間,除了做了一些該做的公益事情外,剩余時間都用在了看書寫作上,有三部中篇小說已脫稿,一部中篇、一部短篇正在生產制造中,還有兩部長篇基本構思好了,有空余的時間,我會抓緊時間讓它們“爬”出來。當然,我也一直在充電,我得想方設法努力突破自己,多給讀者帶來一些美好的享受。
山西晚報記者 白潔
延伸閱讀
杜斌“趙樹理文學獎”獲獎作品《天眼》節選
珠海這幾日日日落雨。一會兒風跑過,一會兒雲馳過,一會兒電閃過,一會兒雷滾過,像沒完沒了的交響樂。壹加壹的業務員在辦公室直叫碉堡了,還不得不夾著文件跑去用熱臉去貼客戶的冷屁股。要不然,宅在辦公室的老板突然間醒悟過來,會把他們罵成一堆垃圾。
張高美閉著眼睛,靠著老板椅,頭上戴著永遠是七彩斑斕的耳機,耳機裡播放的是流行歌曲。他的手下意識地撫摸著桌上的卡通喝水杯,人在流行歌曲裡,心卻不在流行歌曲上。
早餐還在桌子上放著,文員阿虹催過他三次了。
他沒有胃口。
他的胃處於睡眠狀態。
他的腦袋裡140億個腦細胞在上下翻飛,高速奔跑。
他還在思謀黃楊中學太陽能工程項目。他把所有的競爭對手放幻燈片一樣過了一遍又一遍。面對每一個招標項目他都是這樣,投一次標就像是坐了一次監獄,脫一層皮,掉幾斤肉,死幾億個腦細胞,還伴有頭暈、耳鳴、惡心、嘔吐、乏力、視物模糊以及心悸、失眠、煩躁、注意力不集中、思維力低下等症狀。他曾和文員阿虹開玩笑說,我投一次標,比你們女人生孩子都艱難。
就目前的狀況來看,黃楊中學這個太陽能項目,張高美還是蠻有把握的。過去統治珠海各大投標工程的幾家外地公司,像東莞的五星太陽能啦,深圳的鵬桑普太陽能啦、嘉普通太陽能啦,中山的紅日太陽能啦,廣州的天明太陽能啦,北京的四優普太陽能啦,經過這幾年珠海本地多家太陽能工程公司的運作,已經失去主角的位置,隻配敲敲邊鼓。珠海本地的張高美、劉成、由前途、劉天利、王朝陽、王高峰等幾家太陽能公司,充分利用地理優勢,人脈優勢,時間優勢,速成珠海太陽能行業大佬。像黃楊中學這麼大的太陽能工程規模,張高美已大致想好了,扔給外地的幾家太陽能公司每家一兩萬好處費,就能讓他們像寵物狗一樣聽話。關鍵是要擺平珠海幾家大佬。李春生已經讓他秒殺了,現在最難纏的就是劉成。
如何擺平劉成,這些年,沒少浪費張高美的腦細胞。去年在珠海三中太陽能工程項目上,張高美就對劉成使用過手段。他雇了一個小靚仔勾引劉成的老婆,然后又利用天眼無意間發現了劉成老婆的奸情,和劉成一起去捉奸,想以此來造成他后院起火,燒得他昏天黑地,焦頭爛額,顧不上投標的事。誰想,劉成早就想甩掉家裡的黃臉婆,張高美給劉成制造了一個解脫的借口。劉成不但沒有懲罰勾引他老婆的小靚仔,還大度地動員小靚仔立即娶了他老婆。劉成現在的夫人是以前充當小三的電視台節目主持人阿倩。
窗外的雨不知何時停了,陽光透過雲層,投入張高美的辦公室,在地面和牆上畫出幾塊不規則的幾何圖形。當地面和牆上的幾何圖形漸漸消失,最終由馬路上的路燈代替時,張高美一個新的大膽的計劃形成了。他興奮得騰地跳起來,對著空中揮動拳頭,大叫幾聲:耶!又不忘表揚自己:張高美,你真是個天才!
不過,張高美清楚,他這一招現在不能用,一定要留到招標文件發出后再用。從招標文件發出到開標一般二十天的時間,招標文件發出后的第七八天使用這一招最合適。那時的劉成隻能是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嘆零丁了。
高招!高招!不愧是張高美,聰明!天才!張高美又大聲贊美自己。
文員阿虹還在外面辦公室,老板不下班她不敢走。
張高美全身鮮花,一臉朝霞。他對阿虹一揮手:走,宵夜去!
在五月花飯店吃得津津有味,張高美的手又忍不住摸起了阿虹的大腿。
嘁,阿虹嬌滴滴地搡了張高美一把,輕輕低唱,你永遠不懂我傷悲,像永恆燃燒的太陽不懂那月亮的盈缺﹔你永遠不懂我傷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不懂那星星為何會墜跌……
手機不合適宜地響了。
張高美順手接起,沒好氣地問:誰?
對方回答:我是誰不重要,關鍵是我知道你一肚子狼心狗肺。你又要干缺德的事,我會給你記住這筆賬的。人在地上做事,神在天上監察。
你是誰?
你不是有天眼嗎?
我是在老虎嘴裡長大的。
我沒有必要嚇唬你。
張高美站起來。
對方說:坐下。
張高美判斷對方就在附近,扭頭四下裡察看。
對方說:我能看見你,你看不見我,我是神,你是鬼。
張高美吼道:有本事你露出真相來!
對方說:我是神,我出來你也看不見。說著,嘟嘟嘟,電話那邊傳出忙音。
張高美翻看來電顯示:18607××××××。還是前幾天打過電話的號碼,聲音也是那個有點熟悉,沙啞,雄渾,帶點三千年的滄桑,卻想不起來是誰。
張高美脊梁上流下一道冷汗,想和阿虹共度良宵的打算也讓給澆了。他本能地拉長脖子,驚恐地又四下裡看看。沒發現半個可疑對象。
張高美把18607××××××這個手機號碼拉入黑名單。
108粒瑪瑙佛珠在手裡不停地撥動著。
渾身燥熱,春心盎然的阿虹,擰著眉毛,看著張高美,不知道他接了一個什麼電話,咋一下子就從夏天掉到了冬天?
山西日報、山西晚報、山西農民報、山西經濟日報、山西法制報、山西市場導報所有自採新聞(含圖片)獨家授權山西新聞網發布,未經允許不得轉載或鏡像﹔授權轉載務必注明來源,例:"山西新聞網-山西日報 "。
山西新聞網版權咨詢電話:0351-4281485。如您在本站發現錯誤,請發貼至論壇告知。感謝您的關注!
凡本網未注明"來源:山西新聞網(或山西新聞網——XXX報)"的作品,均轉載自其它媒體,轉載目的在於傳遞更多信息,並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