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體 山西門戶
山西新聞網不良信息舉報:0351-4281485
百花文學獎、三毛散文獎獲得者傅菲自然文學力作《深山已晚》節選——
大地的浪漫主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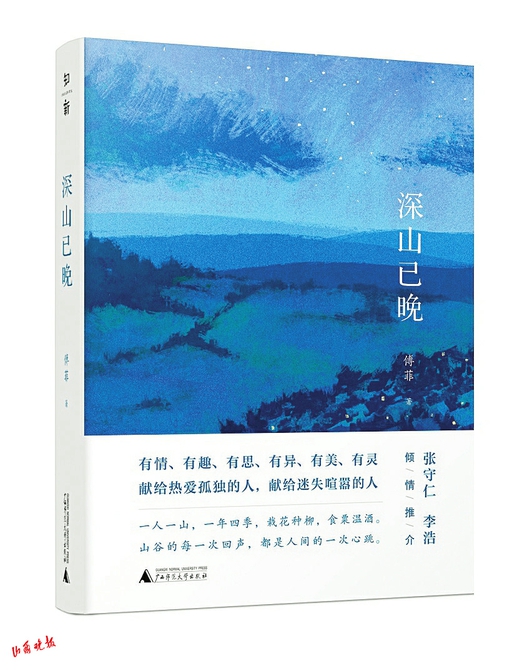
《深山已晚》 傅菲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本書是江西作家傅菲深入武夷山北部余脈榮華山和浙閩群山等原始大山區,客居一年多,和大自然親密相處而創作的散文作品集。主題是發現大自然的美,發現大地萬物的生命價值,進而表達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本書創造了新的山地美學,細致,情濃,奇異,書寫了山中的奇遇、四季風光,以及落日、下雪、蒙霜、暴雨、夜空等美到極致的自然景觀和自然現象,充滿了思辨哲理。文筆優美,詩意叢生。作為自然的布道者與回歸者,傅菲在書中構建了一種人文理想,既有生態自然與倫理情感的美學體驗,也有人文精神終極關懷,充滿了思辨哲理。貼合當下都市人群疲於城市風景,想要回歸山野,尋找心靈棲息地的心理,創造了一個田園式的桃花源,留給人們繁忙生活之余一個安寧的休憩地。
榮華山沒我想象的那樣,高聳雲端,延綿數十裡,山梁交錯,人煙稀落。我來客居第一天,友人對我說:“門口的這座山叫榮華山,有時間你可以爬爬山。”我抬頭望了一眼,相對海拔不超過四百米,林木競秀,四支山梁像四隻粗壯的腳。像一頭臥在溪邊的老虎,半是假寐半是覬覦,有一股雄視的氣概。
說實話,我對山的高度缺乏興趣。草叢間的小路,竹林裡的鳥,遺忘的野花,灌木林,茶地,一片水田……燒荒,砍柴,打獵,採果,對這些,我卻像個小孩,興致勃勃。種菜,割稻,趕鳥,捕獸,作為“觀眾”,我保准是最忠實的那一個。也是最熱情的一個,發煙,送水,說不定還留人吃飯,隻要對方不推遲的話。客居一個多月,我哪兒也沒去,既沒拜山也沒問水,更別說拜訪鄰居了。去過一次山坳,是查勘泉水。山澗水在坳裡,形成一個深潭,幽碧得吸眼。我把毛竹穿洞,一根接一根,把水引到院子裡,養魚、煮茶、洗澡,很是清爽。水嘟嘟嘟地從毛竹管裡流下來,落在水池裡,魚逐著水花,夜晚,水聲清脆,有時間的韻律,別是一番情境。離我最近的鄰居,在山壟下,約有四裡遠。中秋節后,村裡的捕蛇人老汪,到我這兒,見我用勺子掏罐子裡的蜂蜜,問:“你常喝蜂蜜?”我說,什麼都可以不吃,但不能少了蜂蜜,可惜,十年難買一罐土蜂蜜。他臉黝黑,尖尖的臉龐,說話口吃,他說,山裡有個養蜂人,他刮蜜時喚你一聲。
其實也不是深山,繞了三個山坳到了,山路走了一個多小時。山路埋在灌木林裡,生人進不了。山雀嗚嗚地飛,在竹林,在茶地,一群群,百十隻一群,起起落落。山上隻有一戶人家。一戶人也就是一個人。養蜂人六十多歲,清瘦,手指長而剛硬。老汪用方言和他交談。我懂,但我假裝不懂。我送了一袋方便面、一包煙卷絲、四雙厚棉襪給老人。老人執意不要。我說,要不是你住這兒,我還沒理由上山呢,我把這些東西帶回去,你可得付我工錢。老人笑了起來,空空的牙床使得兩頰陷進去。屋檐下,碼了很多干木柴。他是靠賣柴為生的。他從門后摸出一根木棍,帶我去看蜂。蜂在山崖上,一個圓木桶,挂在那兒。老人說,野馬蜂收了,養起來的,養了三箱。另外兩隻箱挂在油茶林裡。我站在崖下,馬蜂翹著長尾巴,嗡嗡嗡,在眼前飛來飛去。不驚擾它,蜂不蜇人。
緩緩的山坡向下延伸,坡地是南浦溪。南浦溪像一條鱗光閃閃的巨蟒,蜷曲著安睡。楓樹和鬆樹,混交在一起,偶爾一叢竹子冒出來。人煙散落在水岸邊或山坳裡。我始終沒和老人提蜂蜜的事,捕蛇人顯然有些失望,在回來的路上,不斷地說:“唉,一個下午全走冤枉路,抵不上捉蛇去。”我也沒應和他。怎麼說呢?心深處奧妙的絲縷,隻有極少數的人可以捕捉的。
差不多有半個多月的時間,我幾乎每天去山間,中午或傍晚去。我採集了很多植物的葉子、花朵和昆虫,隻要是不一樣的,我都收集在標本盒裡。我不去探究這些植物叫什麼,屬於什麼科屬,當我打開盒子,看見那些枯葉和干燥花,我心滿意足。當然,我也盡可能去辨識它們:楊梅樹、楊樹、黃檀、紫荊、山楂樹、桉樹、苦櫧、石楠、野山茶……斑竹、紫竹、桂竹、毛竹、苦竹……蜀葵、酢漿草、麻、萱草、石蘭……在我生活的每一個地方,我都盡極大可能去認識我可以看到的、可以聞到的一切。我的一生,沒什麼宏偉的事情需要我去做,我所有的熱情都會付諸周遭的生活,深深地愛人,融於自然。哪怕我領略的自然僅僅是一個小小的山崗,甚至是一個庭院。
“山崖那兒,怎麼秋分沒到,樹全枯死了呢?”我問雜工老張。老張是木工,也會泥工,人長得粗壯,對這片山地非常熟。他說,那叫苦樹呢,八月全死,樹枝樹干砍下來可做柴火,實際上沒死,到了春天,比其他樹都綠得快,樹葉篩子一樣蓋下來。我們走了半個多小時,到了山崖。苦樹是闊葉樹,葉子肥厚,橢圓形,有鋸齒,有一種澀香味。樹干多枝杈,樹皮灰褐色,會自然脫落。我嚼了一根木枝,甘甜。怎麼叫苦樹呢?或許是每到八月,面臨死亡,多麼不堪。可每到春天,又復活,多麼受上蒼眷顧。山崖上,有許多苔蘚,半綠半黃。苔蘚有筷子粗的莖,一米多長。我還沒見過這樣的苔蘚呢。
山邊有一座寺廟,叫天陰寺。寺廟外,有一片竹林,竹子是方形的。很多人都對我這麼講。老張也這麼講,說,竹子是易種的,可方竹種不活,即使種活了,也成了圓竹。我種過很多竹子,毛竹,紫竹,桂竹,整片地種,竹子是方的,我還是到了榮華山才聽說呢。我對老張說,年底,我們種方竹,掏深洞,埋肥泥,填豬糞,蓋熟土,種竹鞭,五天澆一次水。
山坳裡有雛菊。雛菊貼埂上,金黃色,一盞盞的小燈一樣亮著。我已連續看了半個多月了。前天早上,我去看,路過一片板栗林,五隻喜鵲飛出來。長長的尾巴,嘻嘰嘰嘻嘰嘰。大概十五歲時,我才看過喜鵲和烏鴉。我住在祖屋裡,門口四棵大香樟,喜鵲在樹上筑巢。每年初夏,巢裡會伸出黃喙,毛茸茸的雛鳥在枝丫上跳來跳去。祖父把樓梯靠在樹上,扶梯而上,摸鳥給我玩。鳥沒摸到,抓出一條蛇。恍然間,祖父已去世十八年。秋天的山野枯瘦、蕭瑟,榮華山卻還是繁木蔥蘢,更別說在邊地上有各色的野花。當然,我比較偏愛蘆葦花。蘆葦在地頭牆角溪邊,一蓬蓬地冒出來,油綠油綠,到了秋天,葉邊枯澀葉心發黃,葉子裹著一根脆脆的稈,稈頭抽出一枝花。花白色,細密,須絨軟軟。風吹,蘆葦搖曳,稈頭擺動。山雀、灰雀站在稈頭上,迎風舞蹈。我偏愛它,不僅僅是它有植物線條的柔美,它更像是一種言說:又一年的秋天已至。蘆葦,亦稱荻,又名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給人一種蒼莽且永遠無法抵達的境界。沿著南浦溪,有密密的蘆葦,斜斜地趴在水面上。現在,它幾乎全黃了,蘆葦花白白的,白發的那種白,枯瘦,似乎隨時會被風折斷。如提前到來的暮年。
樹林在山巔上。樹是女貞樹中的金邊冬青。有人說,林子裡有很多鳥,大部分是候鳥,夜間棲留,早晨飛走。看鳥的話,可以清晨上去。我立馬來了興趣,第二天去了山頂。林子裡,有許多白白黑黑混雜的鳥屎,還有一些羽毛。女貞秋天結籽,是鳥偏愛的食物。無鳥可看,鳥或許早早飛了。山並不高,但整個浦城之南,盡收眼底。南浦溪是大地上的腰帶。山巒緊緊交疊著山巒,一直延伸到銅鈸山山脈。山下的盆地,呈兩個菱形,像蜻蜓的兩隻翅膀。但看不到贛東的靈山。靈山北腳,是我的故地。延綿山巒是蒼翠的竹海。
山區的黃昏來得早,太陽還沒落山,暮雲便把榮華山罩住了。投宿的鳥兒,呼啦啦,往林子鑽。我把燈掌起來,望望窗外,榮華山已不見,隻有暮雲沉沉。
暮雲下垂,高空中,大雁列陣而過,呱呱呱,叫聲如暴雨。我開始收拾從山裡撿回來的鳥糞、羽毛、草籽,以及破舊的蜂窩和鳥巢。我也撿蚱蜢、蜻蜓、天牛等昆虫的干體。這些東西,我由衷喜愛。在榮華山,無論是草木、昆虫、鳥獸,還是養蜂人,都是大地上的浪漫主義者。它們和他們知道大地上發生的一切。大地上發生的一切,都與它們和他們生老病死有關。他們和它們,與大地同頻共振。世間萬物,其實很簡單——如何生,如何死。剩下的還會有什麼呢?浪漫主義者,從來不會悲苦,也不孤獨,隻由心性地吹奏和沉默。生也至美,死也至美。這是藝術的最高境界,也是生命的最高境界。抬頭看一眼榮華山,我對人間不再有怨恨。
山西日報、山西晚報、山西農民報、山西經濟日報、山西法制報、山西市場導報所有自採新聞(含圖片)獨家授權山西新聞網發布,未經允許不得轉載或鏡像﹔授權轉載務必注明來源,例:"山西新聞網-山西日報 "。
山西新聞網版權咨詢電話:0351-4281485。如您在本站發現錯誤,請發貼至論壇告知。感謝您的關注!
凡本網未注明"來源:山西新聞網(或山西新聞網——XXX報)"的作品,均轉載自其它媒體,轉載目的在於傳遞更多信息,並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